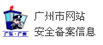一个32岁得了6种癌症的女人
- 来源:智族GQ
- 关键字:癌症,医生,治愈
- 发布时间:2024-01-29 15:22
采访、撰文:肖薇薇 编辑:王婧祎 插画:陈禹 视觉:aube
抉择
“听医生的就好”?
一团粉色闯了进来。王梦琳穿了一件粉色卡通卫衣,一双粉色袜子,走进咖啡馆。她高高扎起马尾,说话时眼睛带着笑意,总是先讲旅途趣事,她与丈夫季理刚从厦门、广州回到南京,假期和表妹们去上海参加了漫展,Cosplay照片里她顶着一头炸裂、软萌的绿色假发。声音爽朗,聊天时百无禁忌。
只是,许多细节会提醒她作为一位癌症病人的事实。她随身拎着一个大大的卡通水壶——一天至少要喝2L水。手指贴了两个创可贴——她的指甲变得脆弱,不经意就会破开。这都是靶向药的副作用。还有甲沟炎、溃疡与脸上大爆发的痘痘,她因此秋日里踩着一双黑色凉鞋。
王梦琳人生的岔路口出现在2005年,她读初三,左手肘偶然撞在阶梯教室的扶手上,肿了起来,之后在医院确诊了恶性骨肉瘤。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经过手术、化疗,她度过了平静的10年,病灶没有复发。这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标准。
2015年,新的癌症再次出现,悄无声息地,有时甚至连肿块的提醒都没有,她又被拽进疾病的漩涡。她依次确诊了乳腺癌、肺腺癌、肾上腺皮质癌、间叶源性肿瘤、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多次手术、化疗,在王梦琳身上留下可见的改变,切除肿瘤的同时,也切除了她的一根尺骨、双侧乳房和一片肺叶。
加倍的打击是,王梦琳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几年前去世。她和父亲做过基因检测,报告显示,父女俩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可以简单理解为,他们抵抗癌细胞的能力极大地弱于常人。
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她暂时没有能够找到阻断癌症发生的办法,只能在新的肿瘤出现时与之对抗。然而,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了6种癌症的人而言,并没有哪个医院的科室、医生能够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连多学科会诊都不能,她每次只能选择一项癌症、一处肿瘤去问诊。“腹部找腹部的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肺找肺的医生,病理问题找病理科。”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听医生的就好”。
的确,一些寻常的小病,我们可以遵循“听医生的就好”,但当疾病变得复杂,新的问题不断叠加,这个原则就开始失效了。每个科室的医生说法可能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就拿去年发现的一枚肾上腺皮质肿瘤来说,有的医生认为是此前的癌症转移,毕竟她已经有过三种癌症病史。但是究竟是哪种癌的转移呢?不同的转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用药方向。还有医生建议,要不干脆切掉这枚肿瘤看看,通过病理检查确定来源。但医生同时又提醒,“盲目开刀切除,会不会反而加速体内癌细胞转移,这都是难以预测的。”
与此同时,术前需要停靶向药一段时间,而那时王梦琳正在吃一款针对乳腺癌的靶向药,一旦停药,病情是否会恶化?她见了许多医生,但没人会帮她作决定,每位医生会给出自己的诊疗方案,也告诉她其中的风险。决策权在她手里。可是,连这么多权威专家都没有定论,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年轻女孩儿,又该怎么作决定呢?
她只能是咨询更多的医生,然后做出一个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的抉择。最终,去年年底,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王梦琳做手术切除了这枚肾上腺肿瘤,在腹部留下一枚核桃大小的疤。命运和她开了个小玩笑,病理报告显示,这枚肿瘤并非医生们此前推测的癌细胞转移,而又是一个原发癌症——肾上腺皮质癌。这是她得的第四种癌症。
再拿肺部的结节来说,去年9月以来,王梦琳的肺部出现了大量微小结节,超过了一百枚,影像报告上是密密麻麻的白色雪花点,看起来令人惊骇,白点仿佛将要把双肺占满。可结节都太小了,无法做穿刺活检。
有医生说,无法排除是此前的乳腺癌转移。她去了此前做乳腺癌手术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生提议,“要不你来住院,做两个疗程的化疗试试看。”
王梦琳犹豫,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现代医学的有限性——当各种检查无法明确,只能通过“排除法”去定位,而这些尝试的代价是未可知的。
她和丈夫去了趟北京寻求“第二意见”。“无法穿刺,什么都没能定性,凭什么认为是乳腺转移呢?”在北京一所知名的肿瘤医院,乳腺科专家抛出疑问。
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就诊时间只有几分钟,她抱着报告单,急切地想要专家给一个治疗方案,和南京的化疗方案对比。“如果你一定认为是乳腺癌转移,我可以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专家语气有些不耐烦,助理叫了下一位的号。
“我就是无法确定才来的啊!”时隔半年,王梦琳说起依然无奈,她没去开药,郁闷地回了南京,决定试试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化疗方案。
化疗后,肺部结节却依然在长。用药、手术、化疗都没用,治疗陷入死胡同。医生最后说,只能等结节长大,继续观察。
今年4月,终于有一颗肺部结节长大到可以勉强做穿刺了。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是此前患过的肺腺癌肺内复发与转移。经过基因检测,她的靶点是罕见的“20插入突变”,在所有转移的患者中只占4% ~ 10%。
这对王梦琳而言,并不完全是个坏结果,至少为期半年多的化疗、手术、试药进程,终于告一段落了。2023年初,针对肺部“20插入突变”的靶向药在国内上市,从4月22日,她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服药。
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8月的一次全身检查,王梦琳身上新增了三处异常:肝胃间隙腹壁上出现一个肿块,直径约3厘米;右腿膝盖下方胫骨处肿瘤,出现了骨质破坏;脑部也照出一处水肿,直径0.7厘米……这意味着,未来,王梦琳还要别无选择地做出更多次选择。
代价
“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保命重要”
从去年切除肾上腺肿瘤手术后,王梦琳就没法再工作了。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在亲戚的公司里做财务,公司在外省,平时她在家用电脑远程办公。
王梦琳两次重大的人生转向,都与癌症有关。2005年因病休学后,她重读了一年初三,却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在父母建议下填了家附近的一所五年制专科学校。因为考虑到高考压力,担心癌症会复发。尽管她的中考分数远超过这所专科学校的录取线。
“现在让我想想看,确实也会有点遗憾。”王梦琳回忆说,但当时她没有提出异议。
与曾差点儿失去左臂,与长达半年的手术与痛苦化疗经历相比,没有人敢冒一次险。确诊恶性骨肉瘤后,王梦琳休了学,住院开始化疗。她对化疗药反应强烈,输液后狂吐,头发也大把地掉。手术后等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固定带和夹板拆除后,又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次年5月,治疗才结束。
一次化疗间隙,王梦琳回了一趟学校,因为太想朋友们了。当时临近中考,同学们都在紧张复习。她去教室打了个招呼,就在门卫室等他们放学,像往常一样,一路上叽叽喳喳聊天,直到分别的路口。
一旦患了癌症,身体就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排序。王梦琳报考了那所大专的财会专业,这是大人眼里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大专的学业确实轻松多了,和读初中时一样,她还住在家里,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她常逛论坛“西祠胡同”,找到了一起玩Cosplay的朋友。2008年南京举办第二届漫展,他们一起排了一台舞台剧,还得了奖。她扮演的角色来自游戏《空之轨迹》,一个戴着紫色头发、很勇敢的女孩。
她做了许多事情去补上学历差距,尽管并不喜欢财会专业,她还是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既然学了,还是把该考的考了。”大专进入最后一学年,她“逼”着自己学完所有专业课,考了会计证书、大学英语四级,如愿找到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她遇到了男友季理,他是隔壁部门的同事。
王梦琳享受那段充实忙碌往前冲的日子。大专毕业后,她去了一家外企工作,做人力资源助理。她还自考了南京大学本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工作第三年,她的职位越来越高,从助理、专员晋升到了主任级别。
她和男友都变得忙碌。她负责做整个江苏省门店的薪资,每个月发工资前几天最忙,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不加班的晚上和周末,她回学校上课,季理就带着工作电脑去学校陪她。一个勤奋的、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女孩儿,然而,癌症再次将一切按下了暂停键。
2015年秋天,公司体检时,王梦琳查出乳腺异常肿块。复查的结果是坏消息——左侧乳腺癌三期,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属于中晚期。这次南京几家三甲医院都给出了确定的诊断。
王梦琳再次被拉回医院,回到那套早已熟悉的漫长的流程:检查、化疗、等待手术、再继续化疗。两年病假里,外企的补充医疗保险派上了大用场,让她不至于有大的经济压力,只是再也无暇顾及事业。
“到那个时候肯定会选择保命重要,”王梦琳叹了口气,“一开始肯定难受,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接受嘛。”
这次手术后,王梦琳失去了双侧乳腺。手术前后,她一共化疗了八个疗程,比骨肉瘤治疗时间更久。她吃不下东西,头发掉得很快,于是干脆剃了个光头。化疗结束,她需要终身服用一款内分泌药他莫昔芬,这引起了强烈的副作用,一开始是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她几乎全天都坐在马桶上,整个人虚脱。
2017年病假结束前,王梦琳回公司,领导体谅地说,建议她换到更轻松的岗位,管理人事档案,她的职级依然保留。她心里一时间涌出复杂滋味,那是她刚毕业做人事助理时的工作内容。
不久父亲也生病要做手术,她需要经常请假,哪怕调去一个清闲岗位,她也无暇应对了。于是,只好离职。
再次求职时,作为一个有癌症病史的人,王梦琳的选择并不多。一位面试官看到她手上的疤,专门问了她,她没有隐瞒,面试后续不了了之。王梦琳自己做过HR,她当然知道癌症病人找工作的艰难。
2017年底,王梦琳去了南京一个做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协会工作,负责与在南京的外国教师沟通。这份工作工资不算高,但胜在轻松,不用加班,还有寒暑假。面试谈好后,对方一直没有要求入职体检,王梦琳也没有提起。她忐忑着心情入职,直到拿到第一个月薪水,才放下心来。
后来疫情暴发,协会关了门,王梦琳失业了。她没再去找工作,而是在亲戚开的小公司里远程工作。2021年初,王梦琳又确诊了新的癌症,情况开始失控,她的身体不断“冒出”新的肿块,她经常需要去医院。
人生完全被打乱了,她再也顾不上其他的事情。
婚姻
“做自己觉得对的事”
在南京的几日,多数时间我与王梦琳约在她家附近的公园。工作日的上午与下午,季理需要去处理一些工作,她就一个人提着水壶和零食包出门散步。
去年他们刚搬来这里,在南京的东郊。原本只是偶然陪朋友来看房,他们却先看中搬了家,这里空气比市区好,旁边就是公园和学校。之前他们就在考虑领养的事情,结婚后,医生曾严肃提醒他们生育的风险,因为王梦琳的癌症病史,“还是领养个孩子,生活更完整一点吧,有点盼头。”双方父母也都同意。
他们把领养计划定在王梦琳乳腺癌手术的五年观察期后,也就是2021年。2020年,季理去福利院咨询了领养的条件与流程。他问过王梦琳,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王梦琳说:“女孩吧。”不一会儿,她改变了主意,笑起来,“还是看眼缘吧。”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新的癌症出现,领养计划也搁浅了。
这一年,季理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有时他们一周五天都要去医院,时不时离开南京几天,去一线城市会诊。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他得赶一赶工作进度。季理现在一家公司做资产评估,上下班时间相对自由,薪资构成简单,多劳多得。领导、同事相识多年,都知晓他的难处,让他远程办公。
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王梦琳有医疗保险,但靶向药需自费,并且终身服用。除了看病支出,他们还有房贷要还,夫妻俩无法承受再失去一份收入。
刚见面聊天时,我不自觉会流露出担忧,爱情与婚姻的责任,真的能够抵御漫长的、艰难的抗癌历程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顾者“撤退”的故事。
2015年决定结婚时,季理听过许多顾虑的声音,“你们现在又没结婚呢,你没必要对她负责。”“后面怎么办,能不能要小孩?”
当时王梦琳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在准备化疗。季理这时提出结婚,他的想法简单,“想让她安心,安心做放疗、化疗,怕她胡思乱想。”
季理很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妻子将终身与癌症抗争。他身边唯一一个癌症案例,是同事的妻子,曾经得过乳腺癌,手术后健康生活十几年了。“都说切除以后,就没事了。”这是他们当时对于癌症最朴素的认知。
结婚并非仓促起意,两人当时已经恋爱四年,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季理比王梦琳大四岁,两人感情稳定后,他就把工资交给王梦琳,一起存钱。季理说,以前总想着等攒够钱,买了房再结婚,不曾想她生病一下打乱了时间表。
决定求婚后,季理先告诉了自己的父母,父母没有反对,反而告诉他,如果他认定了,他们就支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父母还打了5万块钱过来,王梦琳的父母也支持了5万,一起帮他们凑齐了首付。
季理则提到了一件对他很重要的小事。他们每个月会开车回老家,在南京周边县城农村看望季理的爷爷,老人家身体不太好,药盒子堆了一抽屉。第二次去,王梦琳特意买了分装盒,把爷爷未来一个月的药仔细分好,以免他漏吃。
他们就在这些小事里认定了彼此。一个不化疗的日子,王梦琳一早赶回学校做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完成,他们顺路去民政局领了证,下午去买了钻戒,一家人吃了火锅,就这样结了婚。
与癌症的战争,却远比他们想象的都要复杂、漫长。
王梦琳是独生子女,她既是病人,也是父亲的照顾者。那几年,她和父亲住院,夜里都是季理陪护,他不肯假手于人,也无人可替换。白天王梦琳母亲过来送饭,他再去上班。父亲进了ICU那几天,王梦琳坐在ICU门口走廊的椅子上守着,直到两人身上都有味儿了,季理才劝动她去附近宾馆洗了个澡。
许多这样无助的时刻,他们靠彼此支持撑了过来。父亲去世后,照顾爷爷的责任也落在夫妻俩身上。爷爷今年89岁了,去年生病后,生活难以自理。当时王梦琳在医院做肾上腺肿瘤的手术,因为防疫政策病房不能随意进出,那天夜里,季理打了好多电话,才找到朋友帮忙,艰难地将爷爷送去了最近的医院。
季理个子高大,长相憨厚,平时跑项目多了,皮肤晒得黝黑。不同于粗犷的外表,王梦琳感受最深的是,他很细心,病历资料都由他整理,复查从不遗漏提醒。去年手术后,赶上疫情,季理特意买了拆线包,照着网上教程,在家给她的手术伤口消毒、拆线。
10月中旬,我和他们一起去上海,季理挂到一个上海人民医院骨科专家的号。他带了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妻子的疾病史,细致到哪一年做了什么治疗。病历里缺了一项重要信息,王梦琳骨肉瘤手术后,手臂内被植入了一块固定的钢板,病历单里缺了钢板的型号与材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做核磁共振,明确脑部肿瘤。
午饭时,一个手机闹铃响了,季理不紧不慢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粒药,递给王梦琳,晚饭时闹铃又响起,他掏出了另一种药。那两天,他一直拿着手机咨询医生,研究文献,还给国外医药公司发去邮件确认。“好多事情,我自己都记不住,他老记着。”王梦琳说。
季理习惯了对妻子的照顾。他会不经意接过妻子左手的物品,不时拎拎水壶,督促她喝水。虽然她很少主动提及对癌症的恐惧,但他还是能感受到许多微小的变化,她变得更加黏他,有时他忙事情,不经意说一句心烦,她的情绪会一下崩溃。于是,看病之外的时候,他们尽量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散步,晒太阳,一起玩《原神》,下班后雷打不动看两集动漫,每天都会有一个动漫更新,一集20分钟。时间更多一些,就去旅游。
和他们相处愈久,我愈发体会到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持是什么。他们在多年陪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相处方式。王梦琳像一个“小太阳”,她会拍早晨季理逗狗狗“年糕”的视频,和二人的家人、朋友维持着频繁的联系,并在吃饭时分享他们的近日趣事。季理的表妹、弟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总是发信息给她,包括但不限于学习、相亲的烦恼。而季理是后盾。不需要说,在面临如此巨大的残酷时,这种后盾意味着什么。
前路
“关关难,关关过吧”
前段时间,季理买了一本书—《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也是一位癌症病人,患癌10年里,他经历了两次手术、5次复发、4次急诊、6次放疗和3次参与临床试验,尽管治疗过程波折又残酷,但他也马上将度过5年观察期,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
王梦琳看完书,鼓起勇气给作者写了邮件。师永刚很快打来电话,建议她把患癌的经历写出来,“或许能被一些专家团队看到”。
文章发表后,很多平台转载了她的故事。评论区里多是鼓励的声音,人们深知生病不易,看病艰难。也有负面的声音,“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何必拖累家人”。几位亲人被这些话激怒,还偷偷集体去回复,让键盘侠们闭嘴。
其实王梦琳早就看过这些评论,后来她不再点开。我们见面时,她说心情已回归平静,“这个过程是先被拉到胡同里边,再慢慢想开,慢慢走出来。”就算命运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只能好好活着呀。”
父亲癌症去世前,他们去做了基因检测,癌症太过罕见、频繁地发生在父女俩身上,已经不是一句“坏运气”能解释的了。
2021年,王梦琳收到基因报告,87岁的爷爷一切正常,而她与父亲都出现异常:TP53基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报告上的结论只有一句,罹患癌症的风险高于常人。
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突变并不会马上导致肿瘤,但当她的身体内失去了重要的“守门人”,细胞战役就随时发生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癌细胞可能逃过免疫细胞的追杀,爆发增长,直至难以控制。
她的父亲第一次患癌是在44岁。父亲性格内敛,平时话不多,喜欢摄影,一生没什么不良嗜好,生病后只要还能活动,从没有落下锻炼。他原来是一位铸造工人,凭借铸造技术,到了南京一所大学当了大学老师。这是命运垂青的部分。
“说不难过那是假的,”王梦琳说,“没想到我和父亲就像那个词,天选之子。”看到检测报告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雷劈中,她感觉全身通电一般,一下被判了刑,拉入深渊。
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癌症患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可接受一个终身作为“癌症病人”的宿命,绝不仅是想通“命运无常”四个字。
社会学家安妮·卡麦兹(Anne Charmaz)将慢性病患者需要面对的两个交替出现的阶段,称之为“好日子”与“坏日子”,在好日子里,病痛能得到暂时控制,生活回归日常;而在坏日子里,疾病带来的痛苦与漫长的治疗让人无暇顾及其他。随着疾病的变化,那些好日子会缩短,坏日子在延长。
王梦琳频繁地回到那些“坏日子”里:手术室很凉,湿湿冷冷的氧气进入鼻腔,时间就停滞了,你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会结束,恢复清醒、见到亲人;当化疗的药输进去,很快会感到难受、呕吐,头发大把掉落,只能再次剃光头;然后是手术后漫长的、钝钝的痛感,连带着呼吸也痛,一点点适应伤口,直到它结痂。
而癌症必然发生,可能在她生命里的任何一天。那种惶惶不安,或许才是最令人恐惧的。许多时候,王梦琳只是这样平静地讲述着。我们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除了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我无法说出安慰的话。我想,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显得过于无力。
她因此把去医院之外的时间都填满,安排得丰富。追动漫,玩游戏,带着妹妹们Cosplay,去旅游。原来她还在学爵士和街舞,只要不住院,她每天都会去跳舞,最近身体不允许了,她就去散步和爬山。未来她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带爷爷晒太阳、学吉他。
“命运对我不好又好,我身体不好,但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朋友、家人,还有我老公。”王梦琳说,因为她和丈夫都喜欢小孩子,朋友住在附近,“他的两个小孩经常陪我们玩,经常会要找我们。”
她努力在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下活得释然。回忆起当初做乳腺癌手术,术后她哭了,血压飙得很高,病房里亲人护士乱作一团时,她哈哈大笑。刚见面时,王梦琳每次讲起手术的经历,语气都很轻松,而我的表情沉重,甚至不知道什么反应才是得体的。当我真实地与王梦琳相处了几天,我才发现这就是她讲述病痛的方式,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寻常趣事。或许只有这样,过程中的疼痛与残忍才能被消解。
时至今日,她已经慢慢适应了身体的变化,如同当初适应左手、胸部、难以抬高的腋窝,尽管过程很不容易。她的身上有手术的伤疤,和朋友去澡堂时,朋友会下意识避开目光,挡在她身前,而她则大大咧咧就走了过去。
王梦琳说,她早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2016年冬天,她和姐姐去热带的海边,游泳、学潜水,还穿上了好看的比基尼。我看到照片里,她那时头发还很短,显得毛茸茸的,好像头顶着一只小刺猬,她张扬地笑着,比了个“耶”——一个胜利的手势。那时所有人都认为癌症已经治愈,病痛过去了,她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癌症从未真正打倒她。尽管接下来的状况依然很严峻,王梦琳身上的第六个原发恶性肿瘤,右腿的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已经长大到必须手术切除的地步了,而切除很难绕开膝关节。这意味着,之后她或许再也无法跳舞了,甚至无法如常走路。
可他们两个普通人,除了停下来,多跑医院,多问医生,没有别的办法。季理说,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走弯路,不能走弯路,“虽然关关难,关关过吧。”
在南京那几天,我们的聊天总是在我的语塞中结束。中途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采访,一方面是感慨于命运的沉重,揭露伤疤的历程充满痛苦,更无法轻易谈论未来,没有人知道癌症下一次滑落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天天一起散步、吃饭、聊天,她极少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时刻。梦琳比我年长两岁,我们聊恋爱、婚姻与30岁的困惑。有一天散步时,她从零食包里掏出了两只醉蟹,是她妈妈刚卤好的。每当我变得沮丧,她总能敏感地察觉,说些鼓气的话,“过好当下”“开心快乐每一天”。声音显得中气十足。
去上海时,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动漫手办店,逛了整整五层楼,被动漫全宇宙淹没,我们没有再去聊任何癌症的事情,沉浸地捧着手办惊呼“可爱”,最后克制地“带走”了两小只。这也是王梦琳那段时间最放松的一个晚上。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天,北京人民医院一位专家打来电话,他说重新审视了王梦琳的特殊病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或许是介于良、恶性交界处的肿瘤,通过合适的手术方案,可能保住膝盖。”王梦琳的语气轻松了许多,这一次,肿瘤至少留给她一些缓冲时间,让她可以去寻找更好的手术方案。
分别时,我问王梦琳会害怕吗。
“你看到我的微信签名了吗? 4.0T的小马达。”她朝我摆摆手,说,“我现在虽然只有四片肺叶,但是我的引擎是带T的,动力还是很足。”我想,这也是她对命运的回答。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