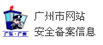朱传一:公益领路人(下)
- 来源:中国慈善家
- 关键字:朱传一,公益
- 发布时间:2017-06-07 14:21
在他晚年的20多年里,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
【编者按】本文将承接此前刊载于本刊三、四月号的两篇报道,继续根据朱传一先生生前文章、信件、录音等资料,介绍他生前另外两件重要工作与贡献,分别是推动社区发展实验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至此,本系列报道结束,诚挚感谢朱传一先生的夫人李鸣善老师对每一篇报道的细致审核;同时,感谢《社创客》主编陈迎炜、益人录创始人宁斌为朱传一先生生前资料的汇整及电子转化做出的贡献。
八、推动社区发展实验
1987年以后,我重点转入了社区发展研究和实验。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加入了“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
“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美国问题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北京财贸学院等联合承担,被列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之一。我们当时研究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并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科学的综合指标体系。过去有一种论调,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自然而然就发展了;或者认为,可以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社会。事实证明,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当时,中国在发展中遇到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第二个是研究“警报指标”或称之为“风险指标”,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课题开始到1989年,我们曾在内部发出数篇有关警报指标的文章。社会矛盾一旦激化成为社会冲突就有可能导致灾难。它们的激化有一定规律,要找出存在于社会内部深刻的根本原因,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和规律。
第三个是建立“社区发展实验区”。社区发展实验,在国外也叫做城市复兴运动、社区建设运动等,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这种实验是由社区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共同进行的。
一般认为,1987年(?)召开的武汉会议是中国社区服务工作开始的标志。其实,这个工作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武汉开始试点,武汉会议实际上是武汉社区服务成就的一次全国推广。
武汉会议后不久,就开始进入了下一阶段,即社区发展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了民政部和崔乃夫部长的大力支持。但是,武汉会议后不久,产生了一种说法:“社区服务是个筐,什么都向里面装。”这使得当时的社区服务内容远远超过民政工作的范畴。崔乃夫部长当时对我说,民政部不能把手伸得太长,也不宜于把社区服务的范围扩得太大、太长,这会引起各部门权责范畴的矛盾。当时,他很明确社区发展的未来应属于基层政权建设,嘱我和司里(?)商议,但工作先不要宣传。
这项工作该叫什么?我主张用社区发展,因为“发展”两字符合科学性,与国际也接轨。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就兴起了社区发展的潮流,联合国为此也召开过专门的会议。但是,崔乃夫部长考虑,还是用建设两字好,因为中国人常说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也相吻合。
经过积极筹备,建立社区发展实验区的构想和条件在1989年臻于成熟。同年11月,在民政部西院召开了“社区发展实验区”的首次会议。在会议中,崔乃夫部长两次讲话,今天我仍记得的是他反复讲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讲话,内容就是要强调实现人民民主,要在基层社区举行选举,产生民选领导班子以管好社区发展及社区工作的重要性。
会后,山东省莱芜市、湖南省益阳市、黑龙江省肇东市得到省委正式批准成立社区发展实验区,并得到省委、省政府的研究部门即各“智囊团”的具体帮助。天津市和江苏省领导也支持开展这项工作。同时,一些地区也开始建立社区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
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借鉴国外的经验。1987年到1993年间,我多次前往美国考察其社区发展运动,建立了不同规模的考察点。我看到的一些美国社区发展实验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区发展计划。这些福利包括社区服务、社区救济、社区住宅建设等计划和项目。以波士顿的南道切斯特区为例,那是波士顿地区的贫民窟,其社区服务以医院为核心,社区服务中心设在医院,从解决医疗问题开始,同时进行救济、福利服务。
第二类是以经济复兴为中心目标的社区发展计划。以波士顿的一个城区中心计划为例,这个计划也叫社区再造计划,重点是把原本环境恶劣的老社区改造成比较适合于居住、工作和生活的现代化社区。那里的老社区原来比较贫困,居民受教育水平低,没有娱乐设施,犯罪率很高。经过工程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教会人员的联合改造行动,那里开设了很多商店、图书馆、医院、公园和各类社会服务设施。读者要借书,图书馆可以送书上门;对于小孩入托和老人吃饭等问题,服务机构都可以帮忙安排解决。
第三类是以解决青年问题,特别是以解决青年犯罪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指标运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个潘达勒斯县,当地青年犯罪占总犯罪的80%。针对这个问题,那里的政府设立了青年社会福利部,专门围绕青年犯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指标统计,还对所谓“流失生”(辍学、逃学者)做了大量研究。我去访问时,他们告诉我,通过社会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和运用,动员全社会关心青少年问题,犯罪率在两年间下降了10%。
第四类是以成人教育为中心的社区教育服务计划。我看过亚特兰大的提高社区群众教育水平的一个计划,他们举办大量教育知识培训班,引导人们求知,通过培训提高就业率,减少犯罪,使社区再度繁荣。
国外的考察帮助我们掌握了做社区发展实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进一步交流经验,我们还邀请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国外学者、专家到国内的多个社区发展实验区访问和讲课,包括当时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社工学院的教授等。
许多年后,再来评价当时进行的社区发展实验区,应该说有一定成果,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总结其深层原因,我以为是,当时虽然有民政部和各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具备经费、人力、学术界支持等条件,但是社区居民群众未被真正动员,社区民间组织未能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社区自治体未能真正建立,民主改革未跟上。事实上,是社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因而形成了昙花一现的结果。
1998年后,中国社区发展进入新阶段,其标志是:(1)政府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逐渐形成共识,政府职能的转移以及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问题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2)由于人口老龄化、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农民进城等问题的日趋严重,社区的作用以及社区服务、社区建设逐渐被普遍接受,民政部成立了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基层“社区服务中心”在一些城市已较普遍成立,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与过去有所不同。(3) 社区组织不断成立与发展, 在一些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研究会、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社区基金会等相继建立,涌现出一些有志于社区发展并具备一定知识和能力的领导者。
1999年7月6日,在北京市社科院、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召集的社区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中国的社区建设工作应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1)人们普遍认识到解决生活问题在社区,项目内容趋向多元化,因而具有较全面发展的条件,出现“单位人”到“社区人”的变化。(2)产业化提出,从市场概念出发,以服务养服务,推动社区产业发展,从以政府经营为主,到以社区产业经营为主。(3)在社区,将三大部门,即政府、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联合起来,各尽所长、所能,形成以“伙伴关系”推动社区发展的趋势。(4)文明社区的提出,从强调“硬件”到强调“软件”,认识到人的因素是社区发展的关键。(5)提倡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如可持续发展观念,建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促进社区发展。(6)进一步提出社会化、民间化、自治化,从政府主导、政府倡导,到政府引导,强调居民的参与以及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直至在城市社区举行民主选举。
九、促进公益慈善事业
199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离休。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主要从事慈善与公益性非营利事业的研究与探索,并认识到单凭政府已难于解决发展带来的众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慈善”是一个被批判的贬义词。1994年2月,“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社论。从那以后,被污名化了几十年的慈善才再次重返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结合自己过去对美国社会的考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人士介绍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和发展。
1994年9月12日,应当时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备组的邀请,我在文采阁做了第一场基金会知识系列讲座,题目是《美国基金会的发展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我指出,基金会具有一种改善社会心理结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研究美国的社区、社团基金会可能是我国学习借鉴美国基金会经验的捷径;基金会主要不是靠政府推动,而是由从事这个事业的非政府组织推动,我们不能一谈到基金会,就眼睛向上,伸手向政府要支持,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新课题。
同年11月,我第一次组织和带领中国基金会代表团前往美国考察。从那以后,中国正式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公益慈善方面的交流。
然而,经过了几年的发展,虽然以广东、上海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都开展了不少慈善活动,但是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对慈善这两个字眼心存疑虑,一些媒体就连在报道由慈善团体组织的活动时也不提慈善二字。所以,我和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等人一致认为,有必要从文化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慈善做进一步探讨,使慈善和社会主义衔接起来。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使我们看到了机会。同年10月19日至20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慈善”研讨会,并邀请季羡林、王蒙、许启贤、郑也夫、康晓光、杨团等20多位专家学者和上海、天津、广东等多地慈善工作者参加。
在研讨会上,针对“什么是慈善”的问题,我提出了现代慈善的概念。我说,现代慈善的标志是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产生了现代管理的含义。对比传统慈善,现代慈善的内容也扩大了,我列举了十个方面,包括扶贫济困、就业、教育和培训、医疗卫生、社会服务、文化艺术、民族问题、科研、国际间的相互支持等。
那是中国第一次以慈善为题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把慈善提到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高度。从那以后,关于慈善的各种会议在国内日益多起来,基金会等慈善团体与各类民间公益性组织纷纷成立。
随着现代慈善在中国崛起,“中国慈善传统的继承问题”被提了出来。1997年4月15日,中华慈善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专门就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我和崔乃夫会长、时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时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商玉生等人进行了激烈讨论。
在那次会上,我提出了四个问题:(1)中国的传统慈善行为是否具有由近及远、由利己到及人的特征?(2)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慈善行为中,政府和民间关系有哪些方面可资借鉴?(3)从中国传统慈善行为的内容与项目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4)如何继承传统与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
我提出,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则与宗族、宗亲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能紧紧抓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资源”,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慈善工作深入中心。
我还从中国的“仓储”和“开仓放粮”制度的历史演变,说明济贫事业从“官”到“民”是一种社会进步。1999年,在爱德基金会董事会的发言中,我重申了这个观点,并指出观察中国民间基金会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联系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东方社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因而产生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与条件各异。我很高兴得知,不是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外国朋友不断在增加着。一些国外专家发明过一个英文词条叫做GONGO,这个字的关键字母是第一个“O”字。前些年,他们把这个“O”解释为Government Owned NGO。后来解释为Government Operated NGO。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这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中国NGO的变化。再后来,我又听说这个GONGO变成了GANGO,即Government Associated NGO。
的确,中国NGO与政府存在密切关系。这点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Partnership)而能促进中国NGO发展的机会呢?中国政府早已提出转移政府职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民间非营利组织将担负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大趋势。
我承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非营利部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无论如何都要能继承资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风尚,也能与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和精神相衔接。因而,我们既有必要从先贤论述中、从历代慈善行为中、从其实践内容中获取教益,又要借鉴于西方特别是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总记得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经营之道》一书中文版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即“不同国家的应变之道各异,应该从中国固有的传统下出发,去寻找应变的良策。”2000年,21世纪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彼得·德鲁克和德鲁克基金会的四位专家的现场论述,使我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
后来,我写过一篇叫做《殷切的期待:从官方报道看政府对NPO政策的前景》的随笔。在它的结语中,我写到:促使NPO健康成长,使之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与道德持续进步的“润滑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NPO,特别是在其初期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与支持,即使是NPO的支持性组织(NPOSO),也离不开政府的信赖和援助。这点与西方NPO及NPOSO的成长历程很不相同,不能把西方对此的观念完全套用于东方。
不容置疑,初生的中国NPO,争取政府的培育和支持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同时,也需要理解政府人员观念转变的艰难过程。当前,政府对NPO的政策和措施正朝向积极方向变化,是值得NPO欢迎的行动;双方出现某些暂时的不协调,当然也是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事。中国NPO不可错过这样的好时机。要理解,这种时机的不断推进和扩大,既依靠政府,也依靠NPO的配合和积极主动争取。
曾经在亚洲一些地区发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和NPO之间存在着“既依靠又自主,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双方相互合作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承认三大部门存在的现实,在具体行动和采取措施方面,大家要多协商、多主动,以多种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和形式的方法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两者间合作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运用已出现的“公办民营”各种形式,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避免僵化。它之所以能获得双方的支持与发展,是由于这种“混合模式”能使政府获得汇集民间人力、财力、智力的效果以弥补其不足;而从民间看,则可借助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增加资源并扩展业务范围,激发社会参与,使大众关切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项目能更有效地实施。
“从慈善起步,不断唤起民众人本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治意识乃至公民意识,不断推进社会改革大潮”,是我个人对慈善未来前景的设想和期望。
整理/徐会坛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