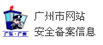诗人
- 来源:江南诗
- 关键字:诗歌写作,生活,诗人
- 发布时间:2020-02-29 21:41
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小县城从事诗歌写作,慢慢就有了隐约的失败感和自我怀疑(尽管,实际上,我对个人写作充满了自信)。但那种边缘的边缘之感,却越来越强烈。自16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三十五年,家人也由最初的支持,变成了不理解和反感,甚至对我的爱好深恶痛绝。
是的,我的诗歌写作没有给我带来巨大的成功和激烈的反响,更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的利益,反而有了不少的反对和诋毁。我深知那些反对和诋毁的根源,也深知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的传承,哪些是因循守旧,哪些是阻力和糟粕。一个当下的中国诗人,若想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得到理解与接受,获得尊重与第一推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文明还远远不到那种程度,还需要有漫长的道路走。且不说我们刚刚遗忘了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文革,那种后遗症是逐渐显现的。
关于生活,无论哪一页翻开,针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沉重的,忧郁的,有着极大压力,尤其是失业以来。那种痛苦与不安,我几乎时时都可以感受到,因为我生存在民间,是毫无社会地位的生活在最底层的诗人。说直白点,是个穷文人。我的诗歌写作建筑在我个人的理想之上,而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是我16岁的梦想。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梦想,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实现了,接下来就是过一种纯粹的诗人生活,这才真切体悟到诗人生活的艰难与困苦。原来一开始我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一条既不幸又幸运的道路。这正应了荣格曾经说过的话:诗人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的。在《分析心理学和诗歌的关系》中,荣格又说:“有一种情况出现的相当频繁:一个长久默默无闻的诗人突然重新被发现了。这是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时出现的,从这个水平来看,过去的诗人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新的事情。这些事情在诗人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但是它隐蔽在象征之中,只有时代精神更新了,我们才能看到它和理解它。它需要另一种更新的观点,因为旧的观点只能在作品中看到它们习惯上看到的事情。”
这里不妨重提先锋。重提先锋,首先就是要对伪先锋给予彻底清理与清退,使叛逆者真正成为叛逆。先锋是绝对不允许冒充的。这是一个阵线,而不是一个新市场,充斥着买与卖,谁都可以到此闲逛、消费或招摇撞骗。对于好诗人来讲,是不是先锋,并不重要。怕就怕滥竽充数、假冒伪劣的先锋及其代言人。当代、先锋这类词语,有它的针对性和时间性,但如今当代、先锋已经混为一谈,哪些诗人是当代诗人,哪些诗人是先锋诗人呢?有谁能够分得清!按道理说,当代作为一个时间段,是较为宽泛的,也有包容度;而先锋作为一批为数不多的叛逆者或现象,反而是严格的,严肃的,正如眼中容不进丝毫沙子。因此,当先锋被某些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时,有的真正的先锋诗人宁愿独立出来,称自己是当代诗人,以示与伪先锋有所区别。比如你可以说某某作品文本带有明显的先锋性,但又称其为当代诗人,这同样很形象很真切地说明了问题。总比泛泛地谈论一帮鱼目混珠的先锋要好得多。?
因此,只有写作和探索时,我的心才暂时平静下来,也忘了周遭的环境。所以,写作的这一时刻,我才是幸福的、愉悦的。也正是探索的这一时刻,才是我所期待的,才觉得残酷的生存还是可以忍受的,从而更热爱生活。
也许,有人至今还在因为我的写作生涯大部分是在小县城展开的而轻视我。却忘了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焦枝线(俗称第二京广线,又称焦柳线)就打破了豫西伏牛山东麓的闭塞,我已经生活在与二十年代的诗人徐玉诺截然不同的境遇下。尤其是七十年代末以来,正值青春期的我,像家乡鲁山一样也纳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我的写作的学习期开始了。这时的鲁山早已没有围城的土匪供我描寫,从而成就我的诗歌事业,成为第二个彗星般的徐玉诺。不,我的诗歌写作是穷尽一生的写作。我的写作是一种全新的写作。确切地说,首先是青春期叛逆者的写作,是八十年代对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叛逆:一种现代派的先锋诗歌写作。这与浪漫主义是有极大区别的。这与“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我的青春期几乎没有受到传统新诗的影响,就很快摆脱了传统,成为反传统的叛逆,并尝尽了叛逆者的辛酸。
从北岛到整个西方文化,我受到了中国和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极大影响,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认识和看待一个诗人,不应以某个地点为唯一的出发点,而应以他的遭遇和感受作为一个客观环境的评判尺度,应以他一生的诗歌作品来衡量他的全部价值和对人类的贡献。更要认真检阅他的影响的范围,从作品风格到作品的深度,以及作品形式的传承,诗歌与地域环境等,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深入了解和认识。
实际上,中国当代诗歌在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经验的积存方面,要比美国当代诗歌逊色的多,更比不上中国古代诗人在这方面成功的令人惊叹的创作,因为在反映现实生活上,中国当代诗歌虚假做作的程度,要比真实的程度占更大的比例。只有少数中国当代诗人,真正的精英,才在真正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经验的积存中,反映出现实生活真实的一面:即处于困境中的诗人的灵魂。
在有的人看来,所谓成功,就是失去记忆,彻底忘记早年同时起步的朋友,而与当今一些所谓的著名人物站在一起,以应“贵人多忘事”的俗语。很抱歉,我不是那样“高贵”,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不会失去写作最本质的东西。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尤其怀念早年的人与事,青春时代,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都与那时有关。一个人的经历,可以千差万别,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背叛那份经历或篡改那份经历,都是不足取的欺骗行为。一个人的历史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不该是虚假的一生。?
而当今的社会,为什么君子和聪明人越来越稀少了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得到的答案是:自私、贪婪、鼠目寸光的眼前利益,使一大部分人昏了头,连一些聪明人也无一幸免,从一个聪明的真诚的人,变成了一个精明的虚假的愚蠢的人。除了钱,一切都不顾了。真正的美德被他们彻底抛弃,代之以当下的以丑为美。我20年前就察觉,这是一个审丑时代。凡是真正好的,都被认为过时了,只有当下才值得拥抱,不管拥抱的一枚伪装的定时炸弹,或是其它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当下并不永远存在,终究会成为过眼云烟,成为令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过往,一个令人惊诧的现象,一个社会学的标本。而真正的现实,还是要从某些诗歌中去寻找,这就是《诗经》和为数不多的真正好的当代诗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欧阳江河和西川异口同声地说:人类的文明是诗歌的文明。
小说家福克纳和诗人勃莱长期蛰居在小镇和农场里写作,人们并没有看不起他们,是因为他们很著名、是美国人?诗人居住在哪里,哪里就是诗歌的中心,很年轻时,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丝毫不为蛰居在小县城而感到低人一等,反而感到一种远离喧嚣的少有的我所需要的安宁。莫言是在山东一个小乡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是在北京或上海,那些热闹非凡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如果在家乡的小县城能买到打折的便宜书,那么我干嘛非得跑到大城市或平顶山去呢?譬如范晔译的《百年孤独》、王家湘译的《瓦尔登湖》、杨恒达、杨婷译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李继宏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王逢振译的《都柏林人》、杨武能译的《歌德谈话录》等,就是在鲁山买的,并且都是印刷精美的正版书。我不否认在大中城市会及时购到很多好书,但好书太多,我却买不起,会徒增痛苦和烦恼,这又是非常不上算的。而把诗写好——就是这辈子,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冯新伟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