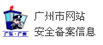10年直面孤独症,做有用的学术?
- 来源:大学生
- 关键字:孤独症,学术,视野
- 发布时间:2024-09-15 20:18
文/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在美国, 每6 8 个儿童中就有1 个患有孤独症; 在中国, 孤独症发病率也早已高于1%。这个数字远高于癌症(1/1500)、糖尿病(1/500)的发病率。不断攀升的孤独症发病率,使得这一精神疾病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易莉已经在孤独症领域努力了近十年。
“从科研中获得快乐”
易莉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然而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还是给她带来不小的挑战:“在北大四年收获最大的,就是感受到周围同学们都非常优秀;这会导致一种心理落差。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在这种环境下,你不得不push自己变得很强。这是在同侪压力下的‘被动进步’。这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周围的学习环境所造成的良性竞争行为,给易莉带来很大的影响。高中时晚上10点就睡觉的她,在大学四年常常学习到半夜12点之后。她笑称:“考上北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强迫症,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除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北大给易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当年学识渊博的一群老师。在她的记忆中,王垒老师的课就像单口相声一样有趣;张智勇老师的讲解细腻深入;还有钱铭怡、吴艳红、苏彦捷、甘怡群、耿海燕老师的课,也都给她的心理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而当年的本科论文导师周晓林老师带领的实验室充满了一种铆足了劲儿做科研的氛围。
在老师的引导和自我严格要求下,易莉努力提高自身的学识,又选择奔赴大洋彼岸,在美国杜克大学继续她的学习。在这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做科研的,本科时其实挺迷茫的,也不知道科研究竟是什么。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第三年,我的导师说我适合做科研,他说我是那种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的人,这非常重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重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下定决心要走科研的路。”村上春树是易莉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她借用村上春树对小说家“为什么写小说”的论述,来表达自己对于科研的感受:“科研其实是一个付出和产出比不高的行业,如果你没有从中获得快乐,就很难坚持下去。如果不快乐,做研究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
回归与安定感
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易莉回到祖国,成为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师中的一员。“在国内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这是易莉选择回国的一大理由。在美国的六年,易莉体会到某种漂泊感。这不仅来自文化上的一些隔阂,也来自内心的不安,国外再好也是别人的祖国。在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内心才感到无比踏实。
回国后,易莉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进行对孤独症儿童各方面能力的研究。事实上,这是她在美国时就一直想做的研究,但由于条件限制,直到回国后才真正开始进行。
毕业多年以后,易莉回到北大参观,发现母校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己还深深爱着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2015年,她申请回到北京大学任职。再次步入燕园,她对这个园子有了更多新的感受。“从我毕业到现在,北大心理系的变化非常大。跟世界顶尖大学的心理学系差距越来越小了。”这里不仅有资深的学术泰斗,更培养和引进了一批世界水平的顶尖学者。这里有无可比拟的浓厚科研氛围,跟各位老师的讨论总是能产生很多的思想碰撞,对自己的科研有诸多启发。2016年,心理学系正式改名心理学院。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易莉不仅开设了本科生课程“孤独症儿童专题研究”、研究生课程“儿童心理病理学”,担任2016级本科生班主任,还带领着5个博士生、1个硕士生开展多方面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从2012年就跟随她学习的学生李天碧说:“易老师平时和学生关系非常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对于我来说,她的鼓励会比拿奖学金之类的事更能让我对学术有热情。”
回到母校,易莉还发现了学生时代所忽略的燕园美景。朗润园、燕南园、未名湖……四季景色各不相同,美不胜收。谈到校园景色,她笑着说:“我希望带着孩子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拍个照,我觉得这非常好。”
“我想做有用的学术”
易莉目前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课题:一是利用机器人教导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二是针对婴儿的孤独症筛查。前者的意义在于,由于孤独症孩子排斥与人的交往,利用机器人可以实现真人难以实现的教导目的,而后者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地进行孤独症的诊断和治疗。由于年龄小的孩子差异很小,孤独症基本在3岁以后才能诊断出来,这是当代孤独症研究和治疗的一大难题。但同时,针对更小年龄的孩子的干预是更加有效的。如果能实现对婴儿的孤独症筛查,将对孤独症治疗产生重大影响。
谈到她所做的研究时,易莉的神情变得格外认真。最初从事基础科研的她,在与孤独症儿童的家长接触中,开始思考很多现实问题。
近年来,我国孤独症发病率不断上升,患者已超1000万(数据来自《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在长期的跟踪研究中,易莉对孤独症家庭的艰难处境有很深的感触:“如果家里有一个孤独症孩子,整个家庭基本都崩溃了。父母至少有一方必须要辞职,陪着这个孩子不停地做训练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是终身的,因为孤独症现在还不能治愈,这对家庭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而且有很多家庭因为这些压力离异了,母亲单独照顾孩子,又无法出去工作,生活特别困难。”
“很多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会问:‘那你这个研究对我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不能告诉他:其实没什么用,就是我们要发文章,需要你这个数据,这样想真的太自私了。他们非常非常需要帮助,甚至是你写一篇科普文章,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干预方法,什么是纯忽悠人的,对他们都很有用。我希望我的研究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现在,当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再问起“你的研究对我有什么用”时,易莉会认真地说明,她现在做的机器人以及其他研究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在孤独症界,人们会觉得,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应该指向干预。我的领域注定了我会比较注重临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能做出什么改变世界的成果,比发什么文章都要重要。”说到改变世界,易莉没有停顿和迟疑。
采访结束后,易莉又与一位12岁孩子的父亲进行访谈。这位家长由于无法确定孩子是否患孤独症而找到易莉,而她需要对孩子的所有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估。窗外是阴沉的天色,易莉打开厚厚的访谈材料,与两鬓微白的孩子父亲隔桌而坐。她温和而认真的神情成为最后定格于笔者心中的画面。
责任编辑:周莹莹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