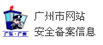韩少功:走出“狂欢下的废墟”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文学,韩少功
- 发布时间:2013-09-11 13:39
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赴湖南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并调至汨罗县文化馆工作。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国作协,并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1987年,与韩刚合译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8年,举家南迁海南,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95年,被选为海南省作协主席,并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促成杂志成功改版,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重镇。2000年,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迁居湖南汨罗农村。
2013年,年届60岁的作家韩少功交出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日夜书》。通过对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大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的描摹,韩少功想展现的是对自己和同辈人的回顾性思考。
“思考”似乎可以被视作韩少功近40年写作生涯的标签。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韩少功一直以思想深刻著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就将韩少功称为“中国文学界少有的思想家”。
从“伤痕文学”时期的《西望茅草地》到具有“寻根”意味的《爸爸爸》;从探索小说的叙事艺术并招致争议的《马桥词典》到新世纪的近作《暗示》、《山南水北》,韩少功的作品几乎出现在几十年来每一次重要的“文学现场”。
始终对社会保持着高度关注与批判性思考,体现了韩少功作为作家的责任与承担。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文坛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迷茫与彷徨,他写作《文学的“根”》一文,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由此引发的“寻根潮”从文学界向艺术、科技、法学等各处蔓延,至今仍时时涌动。
上世纪90年代,韩少功接手文学杂志《天涯》,将其树成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面大旗,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活动和重要命题的提出,大多有《天涯》的参与。世纪之交,韩少功选择辞去职务归隐田园。但他并非做起不问世事的陶渊明,而是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通过亲身感受,对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展开新的思考??
日前,韩少功在上海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操着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韩少功语调始终平静,偶尔会抽上一口烟,陷入短暂的思索。
“我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关心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韩少功对本刊记者说。
有人质疑他如今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敢于触碰敏感的热点问题,韩少功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我现在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惑的、多义性的思考题。”
韩少功称这些复杂的命题需要慢慢梳理,这也正是他现在思考的方向。
有些反思应该从自己开始
《望东方周刊》:在60岁之际推出你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望你这一代人的人生命运与心路历程,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韩少功:这本书算是对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回顾性思考。因为对我最有发言权的是我同辈的这些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一个时间的距离,有些东西可能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处于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变化之多、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新的看法”具体指什么?
韩少功:我们刚走出“文革”的时候,对“文革”的那段岁月一定是有怨恨的,这种怨恨是指向他人,指向时代和社会的。但那个时代和社会不是由抽象的,而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有些反思也应该从我们自己开始。这就需要在一个时间的沉淀后,在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一种状态下回头再看,就能把一些事情说得更平实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回过头看看你们这一代人,你有什么总体的印象?
韩少功: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在时间上我们贯穿了革命和市场两个时代,而在空间上我们则贯穿了城市和乡村。我们处于文化震荡的状态下,所受的冲击很大,自我的焦虑、裂变一直都在发生。还有我们的路途也比较艰难。
《瞭望东方周刊》:知青这一段经历对你和你这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韩少功:知青对我们来说就是社会化的学校。我们走出校门后最先了解的社会就是从最底层开始的。这和我们后辈的情况不大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底部眺望金字塔的最顶端。这样的眺望风险很大,有些人扛不过去可能就崩溃了,成为了牺牲品,很多人对这一段有痛苦的记忆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扛住了,对自己的磨炼、捶打也不是没有意外的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意外好处?
韩少功:就是这不一定是你所设计好的,或是出于你的本意,但它是命运赐给你的财富。
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称你是中国文学界少有的思想家。在小说之外,你的确写出了很多闪烁思想光芒的散文和随笔,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时时“追逼问题”的热情?
韩少功:这首先要谈到作者和文学的关系。有的作者是为文学而生的,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作者可能不必要把自己锁定在某一个固定的文体,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种固定的风格。作者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作者大于文学,大于他自己的写作。作者可以有很多兴趣,我为什么只能写小说呢?我也可以写别的体裁,要容许每个人有写作上自由发挥,全面成长的权利。
我也做过翻译,当过编辑、记者,甚至有时候我也干着和文学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思考也是我的权利,上帝给了我左右大脑,它们有不同的功能,我全面地去尝试一下使用它们,这未尝不可。
所以有时候我会涉及一些思辨性的问题,这在有些作家那里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也很正常,不需要每个作家都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会关注如此多与现实相关的问题?
韩少功:我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关心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奇怪的,舆论泡沫特别多的时代,很多流行的、模式化的思维横行霸道。这就让你可能会有忍不住的时候—“这件事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我想发出一种不同的,反对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在八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而现在的写作中似乎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不再触碰敏感的热点问题,对此你是否认同?
韩少功:这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比如在八九十年代,有关于传统和现代这样两元的命题,要现代不要传统,这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传统在哪,现代在哪吗?很难说清了。
我举个例子,农家肥,那是再传统不过的了吧?但现在又变成很时髦的东西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现在多流行啊。而我们曾经认为是很现代的化肥,突然被发现有很多问题,对土壤土质的损害很大。
所以你现在还能简单地像80年代那样,像个战士一样果断地说“yes”或“no”吗?你会发现传统和现代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需要慢慢梳理。
我现在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困惑的、多义性的思考题。就像我刚才说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命题?“三陪小姐”、贪污腐败这些东西是传统还是现代?你能用传统和现代这把尺子把所有的问题都丈量清楚吗?不可能啊。
狂欢下的废墟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1985年,你写出了“文学的‘根’”一文,也因此促成了“寻根派”或称“寻根文学”的形成,并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你曾经说寻根是为了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那么在你看来,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应该如何重建?
韩少功:简单说,就是价值观的一种迷失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现实的。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们怎么确定这件事情我该做还是不该做?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到底哪一种生活是好的生活?朴素是好还是奢华是好?你能回答吗?你会经常自己和自己抗争。
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像是一地鸡毛,现在我们的文化、思想、学术好像都很繁荣,但是人们的内心是一片废墟,是在狂欢下的废墟状态。这个时候,困难的是我们怎么确定自己有限的目标。
很多人说我们应该把宗教找回来。借助这样的工具来寻找生活的确定性。这是一种方式。是否还有更合理健康的方式呢?这就是我们文化要承担的一个非常艰难的职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宗教会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吗?
韩少功:宗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资源,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对很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可能宗教是比较合适的。乡下的一些农民,和他讲大道理讲不通,只要对他说一句:“你别干坏事,不然雷打死你。”就可能解决问题了,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全社会范围来说,肯定不能完全满足于此。对更多的人来说,还要寻找新的方式。蔡元培先生就曾经提倡以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说中国宗教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蔡先生说的美育是很广义的,基本上可以泛指文艺,甚至是人文学科。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宗教的回潮也是很厉害的,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处于价值观的迷失阶段。有些人是病急乱投医,抓个宗教就溱合着用一下。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韩少功:完全回到宗教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是要从文化上努力。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上怎么努力?
韩少功:还是要有理性的思考。宗教有一些有益的成分,比如劝人多做善事,少做坏事,这对社会安定有好处,也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哲学的思考。但完全靠宗教肯定是不够的,人类的理性思维应该是兼容宗教和科学的,这样的思想能力才会更强大,更健康。
城市和乡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注意到,当年赞同你寻根的很多作家都有着和你相似的乡土经验,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这是因为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接受西方化的过程有一个时间差。城市快一步,乡村慢一步。这个时间差刚好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比对。可以看出两种文明的不同点。
城市要更接近西方一些,而乡村有时候却像一个活的博物馆,更多地保存了我们本民族、本土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这种城乡两方面的生活比较,就比较难看出这样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乡村里生活会有一些直接的感受,很多感性的东西都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是生活赋予你的,这样你进入文学场域就会有方便之处,很多东西可以信手拈来。
我们基于这种乡土经验基础上的写作与以往的乡土文学还不太一样。乡土文学更多的是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一批作家刚好处于城乡之间的剧烈反差的碰撞之间,那种对文明的焦虑是在以前的乡土文学中比较少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马桥词典》中提出了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反思,而你的上一部长篇《山南水北》记录的又是你对于山野民间生活的体察。那么对于今天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你是否有某种焦虑?
韩少功:我也会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有很多的农友。
农村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偏低,这其实是世界性的问题。欧美的做法是把农业挤压到很小的比重,但它依托的是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它们视作自己的“农村”。中国不能重复,也没有条件重复这样的道路,中国的城乡关系怎么处理,还是正在探索的问题。
现在的农业附加值偏低,导致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这是农村现在最大的困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人才。但是人口的回流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因为技术革新等原因,使农业生产的附加值突然增高,超过工业,那时候城乡关系的逆转才会出现。
这一点现在看起来还比较渺茫,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因为现在工业的附加值也在慢慢变低。比如现在的有机农庄,如果能产生足够的附加值,那肯定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学历的人才都会投入进去,不会再呆在城市了。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观察,现在中国农民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韩少功:想挣钱,这是最普遍的民心所向。但是他们也遇到很多障碍,比如资金、技术等方面。现在我们农村很大程度上是靠“输血”,给予各种补贴,但是这样的补贴可持续性比较差,而且是杯水车薪的。在国外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也是靠补贴。但中国农民普遍文化程度要低一些,技术升级的能动性就会比较弱,所以将来该怎么办,还得靠多方的努力。
道德重建与技术主义批判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你就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作了非常激烈的批判。而在世纪之交与王尧先生的那次对谈中,你提到,到9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道德理想”、“人文精神”这一类问题是深化了,也随之消散了。十年后的今天,你对这一观点是否有新的看法?
韩少功:这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虚无主义带来的废墟状态、价值观的迷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前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增强了。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对于道德和精神问题你现在又怎么想?
韩少功:这是一个艰难重建的过程。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现在都处于低谷,处于茫然的时期。我们现在亟需找到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来实现重建。太阳出来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人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总有波动的上限和下限。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种重建有可能的路径和方法吗?
韩少功:当然有。老百姓现在就创造了很多方法。
比如有些人喜欢讲养生,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清理心理垃圾,要清心寡欲,不能利欲熏心。很多大款、老板都讲究这个,少做点坏事,少一点人际纠纷。这就是一种回摆的现象。
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开始重新重视家庭,电视上的相亲节目里,男女嘉宾对对方提条件都有一条是要对自己的父母亲好。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很叛逆,也没有过年一定要回家的习惯,过年都在外面野着呢。现在过年回家变成了一件大事,搞得全国交通瘫痪。为什么现在家庭成为了价值观的新热点?就是因为人们心灵的空虚,需要温暖和寄托。
所以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层面,都会有一些新的社会需求。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迹象。只是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我们价值虚无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判你现在还在继续吗?
韩少功:人对事物的认识过于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人的很多指标量化,智商多少、情商多少,这个可靠吗?我是抱有怀疑的。我觉得人还是要更复杂一些。现在最时髦的语言是“大数据”,但是用“大数据”能准确地描摹一个人吗?
不能否认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现代技术的发展,比如互联网、手机等等都是好东西。技术无罪,技术主义有问题,这要分别来谈。技术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越界了,它超出了适用领域,妄图在不适用的领域建立一种霸权。
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杨天 上海报道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