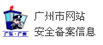18岁,有些事情我不懂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单词,背影,剥削
- 发布时间:2011-07-26 09:54
高三那年的一个周六,传达室葛大爷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张姐。她是我在青年工人读书小组认识的,读书小组解散后,没见过。张姐说:“这一段特别没意思,想找你聊聊。明天星期天,我八点在儿童公园门口等你,你爱来不来。”
第二天,我带着一个单词本去了。张姐说:“你背单词,我怎么跟你说话?这样吧,我考你。你如果把这个本子上的单词都背下来,就陪我说话。”我说:“行。”一个小时的工夫,我就背下来了。张姐说:“这样背单词绝对快,以后每个星期天我都陪你背单词吧。”我也觉得这种方式颇有效率,顿时产生一种剥削人的思想。
看着张姐的背影,我心想,要是有这么个姐姐,倒挺好。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心中又隐隐萌生一丝抗拒,因为我一向以为自己坚强刚毅,希望有一个姐姐,仿佛是心中有一块什么东西融化了,在那种融化的液体中,看到了自己的柔弱。
此后,有五六个星期天,我没有要紧的事,便去“剥削”张姐。次数多了,我有点于心不忍。我说:“高考复习紧张,以后通信联系吧。”张姐说:“好吧,下次是最后一次。”可到了下次,她又耍赖说:“我说的是下次,并不是这次。你知道什么叫‘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吗?”我说:“这首《子夜歌》我也读过,丝就是相思,匹就是匹配,丝线织不成布匹,暗指有情人不能结合。”张姐说:“看你那德行,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我问:“难道我理解的不对吗?”张姐静了静,说:“没有,姐跟你开玩笑。你快回去复习吧。要是误了你考北大,你还不恨我一辈子。”
张姐挥挥手,转身就走了。以往都是我先走,她在后面挥手目送的。我也没多想,转身也走了。
叫姐无数声
此后半年多,我们都没有见面。她给我写过三封信,谈她的工作,她读的书,她的一些思考。我一向是有信必回,在回信中隐隐流露出指导和鼓励的语气,同时大肆炫耀文笔,也顺便算是作文训练。她还冒充我的亲戚,到传达室给我送过一回粽子和一回松仁,我与同学们稀里糊涂分吃掉了。夏去秋来,我收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临行前四五天,我去学校闲逛,葛大爷突然递给我一封张姐的短信,约我在儿童公园见面。我想,也应该跟张姐告个别,就按时去了。
到了约定地点,却没看见张姐,过去都是她先在路边等我。我在四下的树丛里寻找,忽然眼睛被蒙住。我忙叫:“是张姐吧?”她在后面说:“谁是你张姐?叫姐。”我又连叫三声,她才松开。
回头一看,张姐站在绿草地上,穿着水红色连衣裙,乳白色皮凉鞋,头上笼了一条杏黄色发带。她说:“你的理想实现了,感不感谢我?”我说:“应该感谢你,你帮助我复习许多次。”她说:“不对,你应该感谢我的,不是我帮助你复习,而是我这半年多来不帮助你复习,根本就不跟你见面。说你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懂事儿。”我说:“照你这意思,凡是不帮助我复习的人,我都得去感谢吗?”张姐说:“我的意思你怎么还不明白?我要是帮助你复习下去,你肯定考不上北大。”我说:“不至于,你不过是帮助我,看我背得对不对,又不当我的指导老师。我主要还是靠我自己。”
张姐听了,默默看了我一会儿,说:“就你这样的人,也能上北大呀?”我说:“怎么了?我哪里对不起北大?”张姐说:“看来北大里边傻子疯子肯定不少。你走了,有什么话嘱咐我?”我一听有点像孙犁的《荷花淀》,就调皮地说:“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张姐听了,有点奇怪。我又说:“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张姐迷茫地说:“还有什么?”我憋住笑,接着说:“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张姐这下听明白了,“扑哧”一笑,说:“好啊,你占我便宜,我现在就和你拼命。”说着,一把抓住要跑的我,在我身上一通乱打,一边打还一边胳肢,直到逼迫我又叫了无数声好姐姐才肯罢手。
目光织瀑布
平静下来之后,我看出张姐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很像学校里那些落榜的同学。
我说:“你以后给我写信吧。”
“我不给你写信。我直接去看你,不行吗?”
“行,行。”我有口无心地答应着。
“放心吧,我不会去的。连你们中学我都不进去,更不会到北大给你丢人的。再说,用不了几天,你就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看你说的,我孔某人从来不忘老朋友,连小学同学都记得清清楚楚。”
“好,那你就记得我这个老朋友吧。你以后帮助我复习,行吗?”
一提到学习的事,我便如鱼得水,滔滔不绝。
在我说话时,张姐一次也没有打断我。她静静地看着我,直到我自己发现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停下来时,她也没有言语。
我俩相对呆立了一阵。她说:“你说得真好。我就爱听你这么瞎说。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听你这么瞎说了。好吧,我祝你学习进步,生活幸福。”
“我也祝你学习进步,生活幸福。”
“嗯,我有一个请求。”张姐说。
“什么请求?”
“咱们这就分别了,能不能……你……能不能,拥抱我一下?”张姐忽然有点不像平时的姐姐模样,低着头,好像一个小妹妹似的。
我看着张姐水红色的连衣裙,用手挠着后脑勺,故作镇静地说:“拥抱?那,那不太合适吧?我从来没拥抱过,多不好意思啊。不就是告个别吗?以后又不是见不着了。革命生涯常分手,要不,咱们就握个手吧。”我觉得脸热热的。
张姐的脸红红的,她低声说:“我也没拥抱过,不拥抱就拉倒。我是想……我是以为你想拥抱呢,我是替你说出来的。瞧你那一本正经的德行,那就握手吧。”说着,张姐笔直地伸过手来。
我伸手握住张姐那细长的手,她猛地用力握了我一下,挺有劲儿的。我很想回敬她一下,但心里跳跳的,没敢。好像给自己壮胆似的,我连忙说了句:“再见。”
我转身离去。在走向电车站的一路上,我总想回头看看,但努力克制住了。我感觉到后背上一直有一片目光织成的瀑布,从后脑勺往下,淙淙地倾泻着。
(马晓芳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四十五岁风满楼》,本刊有删节)
*孔庆东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