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创新何以变得老旧
- 来源:新智囊
- 关键字:硅谷,英国,创新
- 发布时间:2015-10-13 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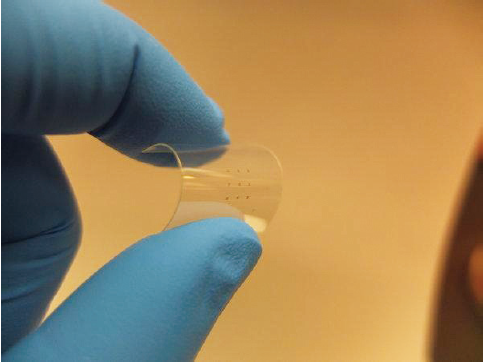
与硅谷相比,英国的创新机制或许显得有些“老旧”。这似乎才是造成英国的创新“窘境”的深层原因,也很值得引以为鉴。
8月14日FT刊登了一篇讨论“英国创新者”的文章,记者莎拉·戈登从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创新如何商业化、政府怎样支持创新以及如何解读创新过程等议题做了一些探讨。不少专家认为,英国面临“创新窘境”。
对于英国的创新能力的评价,不同方法显示出令人困惑的不同结果,也引发出不同解读和观点。如果仅以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衡量这两个传统创新指标平均,英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从事改善英国创新能力的慈善机构Nesta分析说,英国公司的研发支出持续低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竞争对手;其人均研发支出还低于瑞典和芬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排名中,英国在专利申请数量上仅位列第七。然而,如果采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全球创新指数”(GII),去年英国则在143个国家中位列第二,属全球领先的创新国家。
英国前科学大臣戴维·威利特看法是,英国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许多创新也是在该领域中产生的,因此很难以研发等传统指标衡量评价创新。比如,一家律师事务所为金融服务企业提供新建议也是创新,但这“在数据中很难显示出来”。剑桥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讲师迈克尔·吉特森则认为,以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衡量创新无法真正看清全局。“说英国在创新上乏善可陈的观点,最多不过是夸大其词;在最差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个神话——你需要更加丰富、更为可变的多个维度。”
在许多专家看来,英国在创新商业化上表现差强人意。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主管创业孵化的负责人认为,英国在许多基础研究上领先全球,但主要着重“概念形成”, “随后就把这些概念卖给国际企业”,由后者完成优化和商业化——“我们把午餐准备好、做好,但却交给其他人去享用了”。
戈登发现,近年来,英国公司把创新“丢给”了外国企业的案例数不胜数,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以2011年软件公司Autonomy以110亿美元卖给美国巨头惠普最令人咋舌。石墨烯的发展过程,也凸现了这个问题。2004年,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实验室发现这个“神奇材料”。这种只有一个原子的厚度、但强度高于钢,且具备高效导热和导电性能的材料,有许多潜在应用——超高速计算机、可折叠手机,以及超强机翼等。从那时起至今,已有11000个专利及专利应用在全球获批,但其中英国专利所占比例不到1%——亚洲组织的专利占比则将近三分之二。
然而,这似乎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剑桥大学教授Jaideep Prabhu指出,在20世纪初期,化学科学的许多突破都发生在英国,但却是德国企业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规模巨大、利润丰厚的行业。他认为,“在计算机、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等领域也是如此——英国科学家做了许多突破性基础工作,但却是美国‘生产’出了那些巨型企业”。英国创新者们在总体上“缺乏创业基因”。他说, “如果去看一看计算机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就知道他们没有商业化研究的训练,也没有从商业角度看自己的研究的训练”。
戈登在文中提到了总部设在伦敦的PA咨询公司最近进行了一项覆盖15个国家的750位企业高管的调查。这项调查发现,受访人员中有将近一半人将自己企业的创新活动描述为“成本极高的失败”——英国在其中排名第一。据这家公司估计,英国各类企业在不成功的创新上每年浪费650亿英镑。在其中的14个欧洲、美洲和中东国家里,英国在创新成功方面排名第七——排在墨西哥、瑞典、美国、挪威、德国和丹麦之后。但在这个群体中,英国在“最不自信的创新者”和“只谈不做的创新者”方面,却名列榜首。
戈登认为,创新的商业化是一个影响英国经济未来的大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英国公司将创新商业化交由其他国家的企业完成,就会失去本应获得的就业潜力和出口收入潜力。为英国政府提供创新咨询的戴维·康纳尔(David Connel)提到,一位美国来访者说,英国的创新企业“不过是些效率蛮高的小牛皮革厂”。他认为, “如果英国要想创造出更多像戴森(Dyson)、Arm和沃达丰这类企业,就必须制定一系列(支持创新的)政府政策”。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吉姆·罗克斯的创业者经历,说明国家支持十分关键。对从事花瓶设计的罗克斯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到制作样品的生产厂家。他起初认为“这很简单”,但随后就“触了礁”。在英国,生产制造极其昂贵;虽然中国制造成本较低,但工厂要求的最低订单是10000件。“制造厂家对于我这个初创企业完全不感兴趣”。最终还是由于欧盟的“欧洲企业网络”计划,他才在捷克找到了一家工厂,愿意以他可以接受的价格生产他的样品。
英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试图支持创新的各种不同机制,对于这些政策专家意见并不一致。威特利认为,其中最大障碍是20世纪70到80年代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公众资金在科学方面的投入,只应该放到早期研发阶段。他的看法是,关键技术的培养应该从早期一直到市场推广。康奈尔则认为,政府需要鼓励其相关机构将研发项目合同交由初创企业和小企业完成,理由是这样做有助于在英国保留人才和工作机会,减少对于风投资金的需求,并因此让创业者保持对自己企业的控制。
在这篇文章中,戈登多次提到吉特森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倾向于以创造新产品衡量创新,而没有仔细观察创新的过程;尤其是没有考虑创新的扩散——恰恰是创新的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创新本身往往是混乱的,也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康奈尔也说,“真正的差距,在于建立关系网络。人们不仅需要资助和补贴,他们还需要信息和知识。我们在思考创新的时候,应该把它想成一种以接触、沟通为基础的活动”。
政府是否应该直接介入“商业化”的问题其实很值得探讨。支持者的观点听上去有些道理:创新的商业化过程投入高、风险大,企业往往无力完成。然而,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政府不应该把公共资金用来“选秀”,况且政府本身并不具备 “选择”和“支持”的能力。从文章中专家的讨论看,与硅谷相比,英国的创新机制或许显得有些“老旧”。那边讨论的是“如何(以创新企业)改变世界”,这边还在讨论技术如何商业化化;那边是用大规模私人投资“砸”出成功,这边还在讨论政府支持和研发投入失败。这似乎才是英国的创新“窘境”的深层原因,也很值得引以为戒。
相形之下,威利特和康奈尔对于创新过程的探讨值得细想。从英国的经验来看,仅以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衡量,或者从新产品的产出衡量,恐怕无法衡量由这些创新产生真正的“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环境中,需要探讨的可能是形成可以与硅谷竞争创新机制,将创新在“本土放大”;而在我们这里则要面对大量持续积累、但似乎永远无法用市场衡量的“创新”——其中许多是由政府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支持的无效工作,如何从策略、衡量,以及机制等多方面彻底变革,让这个局面不再持续下去。
去年《地心引力》获奖的时候,英国人曾经说,这是个英国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视觉策划和执行”都是英国人做的——美国人只不过出了“两张脸”。美国人一定不会认账,因为这部片子的制片公司是华纳电影公司。如果以最终产品的收益去看,可以将此解释为英国在创新商业化上的“窘境”。然而,如果把创新看作是全球范围的“接力赛”的话,或许其中本身就存在阶段性分工,英国的强项就在于“发现”和“创意”,而更大规模的商业化风险,恐怕要由拥有更大“统一市场”的美国(甚至中国、印度)来承担。以此而论,英国可以不必为“商业化糟糕”而烦恼;而在我们这里,恐怕非要在商业化“较真”才行。
李晨晔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